在日本上空感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一次次想出国,却一次次被拒绝,因为我是被禁止出境的、上了黑名单的。
在杭州的家居住时, 我甚至都不能去萧山。虽然萧山也是杭州的一个区,但我不能过钱塘江,我家门口 24 小时都有人值守。有朋友过来看我,要被盘问,还要被拍下照片、人像识别后通知他户籍地的派出所。他还没回到自己家,警察就已经在他家门口蹲守了。
所有的朋友都很紧张,都为我担心,也为他们自己的安全担心,所以我的朋友越来越少。坐了 16 年牢被释放后回家了,表面上获得了自由,其实还是在监狱里,跟坐监狱没有任何区别。
每个星期,警察都会把我叫到警务室,用各种理由把我叫过去。有时候我发火了,因为我已经是 70 多岁的人了,那些年轻警察本可以上门来找我。
我到了日本佐世保市,一直都还没看到一个警察。我还经常问外孙女,日本的警察是什么样子的?有一天我们去美军基地,总算看到一个交警在维持秩序,她告诉我,那就是警察。
在中国的马路上到处都是交警,到处都在罚款。在日本看不到什么警察,但也没什么交通事故,我也没看到有人吵架,这里的人也没有戾气,所有人的性格都非常内敛,因为他们有一种满足感,不像中国人那样紧张和焦虑。
我感到这里的自由是充分的自由。当飞机还在云层里穿行时,我的心也在云里飘过。当我看到下方海面的粼粼波光,看到那些船的航迹,我问空乘人员:“我们到日本了吗?” 对方回答:“快了,快了,马上就要下降了。”那一刻,我全身的轻松感是无法形容的。我的心理和生理都有反应,整个腹腔、胸腔里只感觉到快乐,就像一股压抑已久的气息,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吐出来,人一下子轻松了,心里郁积多年的东西一下子排遣出去了。
在中共那么高压的统治下,人怎么可能生存得下去?
(旅居日本的水墨画家宇宙大观《中国人权英雄画传》中收录的朱虞夫画像和传记)
十余年中共黑狱,被盯着如厕、睡觉
我很不幸患了癌症,是胃癌,主要原因就是经历了十几年的牢狱生活。我曾在狱中的绝食也可能是导致胃癌的原因之一,对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坐牢,而且我也愿意长期坐牢,但没有想到监狱里面还会有酷刑对待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监狱不让我随意读书看报,允许看的报纸只有监狱的报纸、改造的报纸,除此之外,任何有文字的东西都不能看。
我每次上厕所时,都会被三四个所谓的“帮教小组”的人盯着,也就是帮助共产党来教育我的犯人。这些犯人会先到厕所里面清场,把之前上厕所的人留的下报纸都处理掉。不允许我阅读任何文字,也不允许我讲任何话。
我被关在监狱三个月后,地方的国保大队到监狱来,他们之后也经常来检查,问监狱 “这个‘货’放在你们这边,你们管不管得牢?”。所以中国的司法根本就不是表面上的“公检法”,根本就不存在法治。国保的人对我问长问短时,我才发现自己连语言的能力都失去了,想说一句话,虽然脑子里有这句话,但嘴巴却说不出来,因为我平时不能和任何人讲话。
我上厕所,他们也要清场,把里面所有大小便的人都赶出去。其他人守在门口,由一个人跟我进去,我大便时他就坐在我对面。我要求他,“稍微离远一点好不好?”,但也不行,所以我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
我 24 小时都被监视,我睡觉时他们就坐在我床边,开着灯,看着我的一举一动。有一段时间,他们不让我睡觉,我睡着了他们就马上把我推醒。那个“帮教小组”的家伙是一个搞走私的,走私摩托车,他是通过关系来到我这间牢房。因为我们是重刑犯监狱,关押十年以上的刑期,无期徒刑和死刑的。十年以下的都关在其他的市级监狱或者区级监狱。
监狱要求“帮教小组”对我的一举一动,每句话、每个动作都要写下来汇报。
以“哀兵求胜”的心态注册中国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发源于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的总刑期超过了 1000 年。这是十分罕见的,也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民主党是在王有才的主导下,由王东海和林辉三个人一起去浙江省民政厅注册的。杭州是中国民主党的发祥地。在组党筹备期间,王东海问我对组党的看法,我说组党好。
为什么呢?因为 1998 年的时候,国际社会的白左思潮非常强大,他们已经被当时中国当局的假政治改革所蒙蔽。当时中国当局自称要进行政改,但实际上他们从不搞政改,反而千方百计围堵中国民主运动。我们从民主墙时代开始就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必须被清算,必须从根本上铲除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决不能只是休止,必须彻底结束,否则明天又可能卷土重来。当时我们已经清楚地预料到,如果再出现一个强人,完全有可能重启这场灾难。这就是我们对中共当局的认识,对它们是从来不抱任何幻想的。但是要去做,就要面临牺牲,就要付出代价。
那么,谁来付出这个代价呢?对于我朱虞夫来说,我是一贯的。我跟吕根松讲过,“坐牢让我去,我在里面和他们斗,我有经验。你们年轻人尽可能在外面活动,你们精力旺盛,也可以让更年轻的人继续上来。”
建立中国民主党的初衷之一就是检验中国政府是否真的开放。中国政府号称开放,但我们要试探一下,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开放。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尝试,试探中国政府的底线。当时我个人的做法是“以身试法”,“哀兵求胜”。我们都到牢里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人权状态,让整个基督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政治生态。
当时中共有人讲,中国不要民主,民主已经足够了,因为也没人提出来,没人要求。现在我们要求了,我们提出来了,把球踢到了中国政府的脚下,看他们如何应对。我们当时的两大诉求,其中一个就是开放党禁。1998 年,中国政府要在联合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是一个大姿态,做给国际社会看的。但我们认为,它只是作秀,不会有实质性的内涵。那么,用什么来证明呢?就用我们的遭遇来说明,用鸡蛋去砸向石头,凭借自己的勇气,凭借自己的付出和牺牲去做。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但我感觉到我应该这样做。
王炳章对中国民主党的创立功不可没
中国民主党的成立,与王炳章先生有着骨肉关系,无法切割的关系,王炳章先生功不可没。1998 年这一事件在海外仍然被传为佳话,我对此有切身体会,我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历史有迹可循。
1998 年 2 月,王炳章先生放弃了国外优沃的生活环境,放弃了他无量的前途。他作为第一批留学生归来,他本来有资格做卫生部部长,甚至可以说非他莫属,他却选择了走这条充满着血与火的荆棘之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对我来说,他是榜样,也是先驱。
当民主党成立并去注册时,民政厅说:“你们的材料放在这里,我们会考虑考虑,向上级汇报研究。”这句话纯粹是官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他们自己说过的话不算数。等到克林顿总统离开中国后,当局就要开始打压我们,这一点我和王炳章先生看法一致。他也非常焦虑,嘱咐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做大,放弃这次机会以后,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
王炳章先生让我们走上街头,大量发展成员,扩大民主党的影响。然而,从中国老百姓的素质来看,并不乐观。我和祝正明、吴义龙拿着中国民主党的宣言和传单,走到武林广场。当时,小汽车停在那儿,车窗打开,我们就把传单放进去。那些人都是当官的,过了一会儿,传单就都被扔出来了。我们捡回这些传单,我们感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利益。这么多年残酷的高压政策,让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大家都担心这样的反革命行为会导致被抓、被枪毙,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事不能做。
虽然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但相比之下,现在的环境更加严厉。现在你打个电话,当局马上就知道。你还没出门,他们已经上门了。
所以当时王炳章先生讲过后,我就走上街头,散发中国民主党的宣言,能发多少发多少,能影响多少人就影响多少人,对象都是一些草根阶层的人。
民主发源地杭州 点燃各地组党运动
杭州是一个发源地,当时我们搞了一个活动,让大家都到我们这里来。大家都是来取经的。当时我们也考虑到,还有很多在西北等条件较差、路途遥远地方的人,他们有的走不出来。我们于是决定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正好当时吴义龙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他的论文已经送审,还在等待结果,没有事情做。毛庆祥和王荣清忙于生意,而我在房管局工作,也走不开。于是我们几个人把钱凑起来,凑路费,让吴义龙去全国各地找民运人士,希望大家都来成立中国民主党,成立各地的筹委会。
我们浙江民主党的筹委会与各地的筹委会是平等的关系,不是兄弟关系,更不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我们并不是占山为王,而是我们搭台让大家来唱戏,把这个民主的戏唱好,把中国的人权往前推,把中国整个的政治生态向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民主党成立的意义是非凡的,虽然现在习近平在中国更加残酷镇压中国民主党,同时在高科技、大数据的全面控制下中国民主党在国内发展非常困难,但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民主党在海外的发展却非常迅速。特别是在王军涛、陈立群等人领导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多年来一直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发声。几乎每周都会在纽约时代广场进行集会呼吁,这让我们感到十分鼓舞。
中国民主党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反而在海外不断发展。而且,与国内的民主党人,无论是在明还是在暗,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王军涛先生的做法得到了我们浙江所有朋友的认可。陈立群女士也是我们浙江中国民主党建立时期的创党人员之一。可以说,我们这个火炬没有熄灭,他们还在高高地举着。
老子说,德不孤,必有邻。我感觉我们在美国,在其他很多地方都有知音,一直是在孜孜不倦的不断追求和努力,所以也给我们身在国内的人增加了信心。
作者: 刘畅/整理
2024 年 8 月 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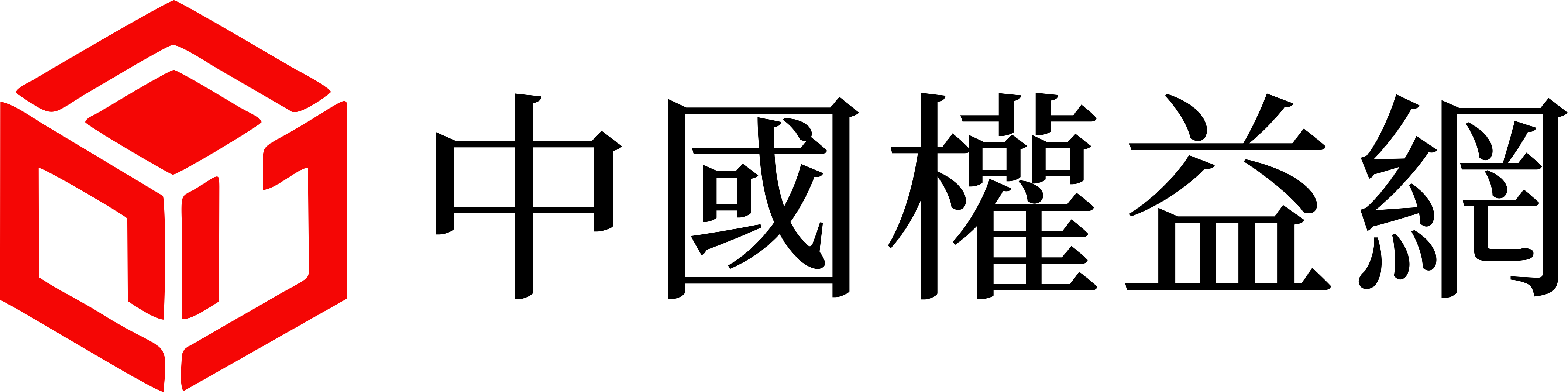

dasd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