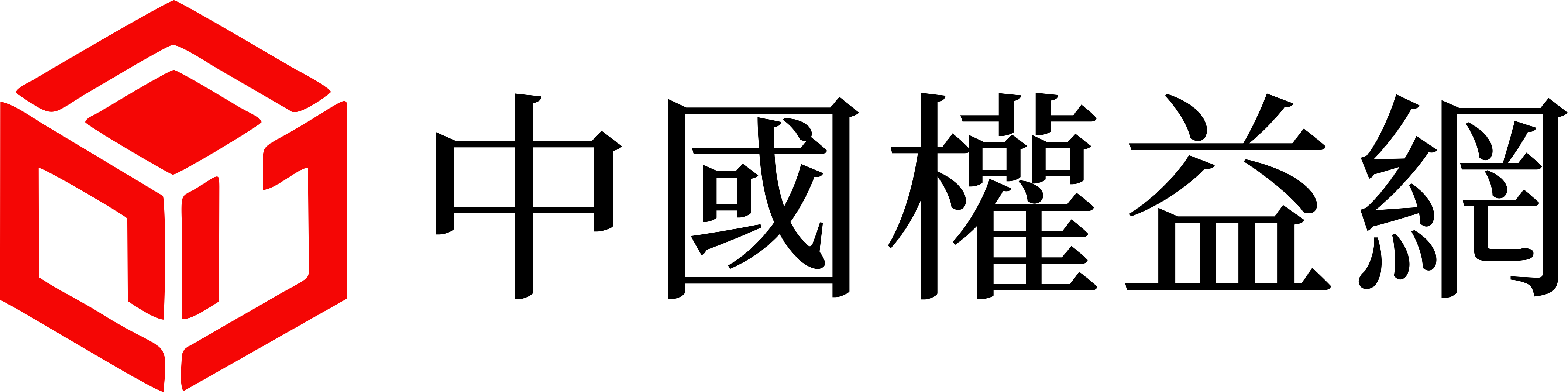【高瑜专辑:口述历史】自由亚洲电台: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之四)
作者: 自由亚洲电台张敏
民运历程
*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简况*
高瑜曾在中新社工作,1989 年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停刊,同年 6 月 3 日高瑜被捕,1990 年获释。
1993 年她再次被捕,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 6 年,1999 年出狱。
高瑜女士多次获国际新闻奖。例如,1995 年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同年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2006 年她第二次获得此奖。
2006 年 10 月 24 日,高瑜出席在美国的颁奖典礼领奖。颁奖典礼前后,我在高瑜下榻的宾馆对她作了共长达三小时以上的专访。以下请听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之四。
*高瑜:“文革”中走出中国人民大学,在雁北农村八年*
高瑜女士在上次节目里谈到——
高瑜:“我对‘文化大革命’痛恨极了。‘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家,我就能够接待我的这些家庭惨遭迫害、母亲坐监狱的这些中学女同学。”
主持人:“那您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延长了在校时间,六年之后……”
高瑜:“(延长)一年。”
主持人:“本来你们中文系是五年制,后来……”
高瑜:“我下农村,八年哪。我们那年毕业分配……等于一个北京名额也没有。”
主持人:“您说下农村八年,是到什么地方?”
高瑜:“山西大同,雁北。”
主持人:“一直在雁北八年吗?”
高瑜:“八年。”
主持人:“从事些什么工作?”
高瑜:“我当过农村的中学教员,还被县里调出来给每年的‘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写材料,全县的,给他们整理材料。那就是相当于以前的‘劳动模范’啦这类的,还相当于‘党代会’了吧。”
主持人:“那那个年代,您自己对社会上所搞的那些号召的东西、流行的东西,有什么独立的看法?还是当时基本上是跟着走?”
高瑜:“这个无所谓是跟不跟哪,别的人教书,把我调出来了,因为我的笔杆子能够被他们所用嘛。写的材料好像当时还在《华北民兵》上什么的发表过,还写过女民兵什么这些东西。当时我就是……调我去,我就说‘尽量给写好吧’。
但是我最根本的……我实在不愿意在那里待。我也没有什么‘党指向哪儿,我到哪儿’,对这种,我绝不盲从。我那会儿就是想回家,想回到母亲身边,想到北京工作。”
主持人:“您父亲是 1955 年……”
高瑜:“去世的。”
主持人:“后来妈妈一直没有再嫁吗?”
高瑜:“没有,没有。当时很多给我母亲介绍对象,当时河北省省委书记林铁的夫人和我母亲在一个单位工作,就给我母亲介绍很多,我母亲都拒绝了。”
主持人:“您母亲是从多大岁数开始……?”
高瑜:”我母亲岁数当时也不小了四十八岁了,一直到八十多岁,就是这样。”*高瑜:空军总院几位军人作媒,我与先生赵元康相识*
主持人:“您自己从中国人民大学出来以后,在山西农村八年,后来是怎么恋爱成家的?您在前面提到过,在人民大学读书时,曾经有研究班年长的同学给您写过求爱信,您当时没动心。后来情况是怎么样?”
高瑜:“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她的亲戚是空军医院的,所以就带着空军的一大帮子,当时他们给我介绍对象,那天晚上我们家一下来了八、九个解放军。”
主持人:“那时候还在山西吗?”
高瑜:“我在山西,我回家来,过暑假来了是怎么的,回北京。当时给我介绍对象,有空军总院的姚院长,郝主任是高干科主任,还有一个技术部的林主任,一大堆都来给我作媒人来了。我也不知道,我说,怎么一个比一个老啊?”
主持人:“您那时候多大年纪?”
高瑜:“我 26 岁了。哎——最后一个,我看他年轻点,还有连他哥哥也来了,都是空军。好,来了一堆解放军。当时给我介绍对象,就说什么‘小赵同志忠于毛主席,对同志的阶级感情深厚’——这是对他的介绍。
后来呢,我记得吧,他一个礼拜来了九次。哎呦,——我觉得,我呢,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跟他,这个人呢,还有点意思,给我们讲笑话。
媒人介绍完了就都不来了,他来了九次。”
主持人:“就是您先生……?”
高瑜:“啊。来了九次。我当时在农村工作。后来听说呢,为什么都是空军总院的,因为他当时是空军政治部的,空军政治部正好领导空军总院的运动,这些人和他关系也不错,曾经把护士医生没有结婚的花名册……让他挑,结果也不知怎么的又‘拐到’我这么个下放农村的大学生这儿来了。
结果他来了九次,我也跟他没什么话说,他就给我们讲笑话。
——说,他们空军有一个(张)医生,胆子最小。有一次下乡去下部队还是什么,人家一伙人就看见这个张医生在老农那儿……那会儿不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吗,老百姓卖个鸡蛋都是‘长了资本主义尾巴’,都要被‘割’嘛,他竟然买了一个塑料袋……看见他从农民那儿。
很快,他们这些小伙子呢,就跟张医生开玩笑,马上打电话到张医生房间,说‘你是张 XX 吗?’,那人说‘我是’,说山东话。他说‘你知道我们是哪儿的吗?’(张)就说‘不知道’。‘我们是公安局的’‘公安局?公安局找我做吗?’‘你是不是刚才到农民市场买了一个塑料袋?’他说‘是,是啊’,‘你知道你犯错误了吗?(知道)你是在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把那个老医生吓得一脑门子汗。
最后啊,他们哈哈大笑,人家才听出来是他们几个捣蛋鬼的声音……
就把我逗笑了。
以后,对他印象就比较好了。我当时呢……因为我弟弟都是一米八三的大个子,他一米七多的个儿,我当时嫌他个儿矮。”
*高瑜:同学朱丽南因“文革”遭遇住在我家,她看见赵元康,说“打着灯笼都难找”*
高瑜:“(我的中学同学)朱丽南,当时她爸爸早去世了,是贺龙部下。她妈呢,被弄秦城(监狱)里了,八年没有音信。作为朱辉照的夫人,押到秦城了。朱辉照是空军第一任民航局局长,已经去世了,结果斗贺龙的时候,让(朱丽南)她妈陪斗。
朱丽南呢,家已经没有了,原来住在帅府园里边那个‘寡妇楼’,都是将军夫人嘛,他们家最后呢……她妹妹更可怜,原来到内蒙,后来没办法,到江西老家去了。她妹妹长得很漂亮。
朱丽南呢,在北京东单菜市场’支左’,卖菜。就等于我的家就是她家,经常是这样。我妈呢……我妈这个人你就知道了……当时都是怕连累,杨成武他们家挨斗,我那几个同学带着……也躲我们家,当时她们有的说’阿姨,你看我们净给你惹麻烦’,我妈……这个我都不知道,是朱丽南跟别的同学说的,别的同学在我们 (近年) 一块儿吃饭的时候 (告诉我),现在都是六十多岁老太太了,我才知道我妈跟她说’你们放心吧,就把我家当成你们家,别说是你们了,就是刘少奇的女儿来,我也敢接待’,讲过这种话,我都不知道。朱丽南当时住在我们家,也看见赵元康了。”
主持人:“就是后来您先生。”
高瑜:“她说‘哎呀,我告诉你,小赵就不错了,打着灯笼难找。你不信,你……”
主持人:“比你您大几岁?”
高瑜:“大五岁。”
主持人:“他当时是不是高级干部?”
高瑜:“不是,不是,就是空军政治部的一般干事。朱丽南说‘小赵这样的打着灯笼都难找,不信你上我们家门口看去’。她们家在王府井大街,净是大兵。我们俩真的跑王府井看解放军去了,她们家就在帅府园里头嘛。所以我们女孩子的那种…… ‘文革’那种现实吧……但是我们还能相濡以沫。”
主持人:“那您的先生是部队出身,对当时社会共产党的教育应该是一直比较能够接受和服从的,那后来您自己走的这个路,比方说一步步从‘文革’,然后到‘改革开放’年代……您自己的变化,到底是从‘文革’中开始了呢,还是‘改革开放’年代?还是更晚,到了 1989 年?”
高瑜:“最终就是‘文革’。我对‘文化大革命’痛恨极了。朱丽南她家……她妈坐监狱去了,八年监狱,身上……就知道叫什么号,连名字都不知道是什么,一块毛巾用得像核桃那么大,出狱的时候,就用那块小核桃那么大的破毛巾在擦脸。”
*高瑜:刚结婚就遇林彪“九。一三”事件,先生进了“学习班”*
主持人:“您在‘文革’时开始后,对政策、共产党搞的这些政治运动有些经历以后,有些看法,那您先生和您的想法是不是一样,他怎么看?”
高瑜:“我跟你讲真话,他也是遇到很坎坷的。我们俩刚结婚,1971 年夏天结的婚吧,秋天就是(林彪的)‘九。一三’(事件)。
他当时在空军政治部工作,立刻就全……
那天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他们机关里都是最表现不好的、不受重用的一批人,忽然跟他讲,给他们都进‘学习班’了,给他宣读很多规定什么的。当时,他们部队的人说‘就你,凭什么对我这种态度?’
临走时(我先生)他还留了个心眼儿,说‘你给我一本语录’,那人随手就给了他一本《林彪语录》,也不是怎么的,他可能也是有些‘感应’,他说你给我《毛主席语录》,那人说‘都一样,都一样,啊。现在手头没有’。(我先生)就进了‘学习班’。
他是(在)当时最低一层的‘学习班’,因为空军最高的是中央的‘学习班’,那就是‘小舰队’那拨儿了。第二批的也是些和上边关系更……负责任更大的一些吧,是北京军区那个‘学习班’,像林豆豆都进这个‘学习班’了,还有一些处长什么的,我都很熟的人。(我先生)他呢,在空军学院的‘学习班’,就是现在空军指挥学院,在里边进那个‘学习班’了。”
*高瑜:我刚怀孕,先生进“学习班”偷写信托陌生人寄来。他回家时孩子已八个半月*
高瑜:“我当时刚怀孕。(笑)他就在那儿了,这样我们根本见不着面了。
我还记得,我当时在山西农村教书,忽然接到一封信,上边写的第一句说‘亲爱的妻子……’什么的……我说‘这是给谁写的?’(笑)因为我们俩好像从来也没怎么写过信,因为在一起嘛,有时候定期一个多月我就回北京了。
他是怎么样?他那天在劳动……他老要求去劳动,因为比在屋里可以接触(外界)吧。他在劳动……偷偷写好一封信,他看见一个过路的,就投给人家,说‘请你帮我把这封信寄了’。
哎呀,没想到那个人就贴邮票给他寄了,我这样就收到这么一封信。
我后来给他回了一封信。听说……不是他说的,别人后来告诉我,说他拿到我那封信哭了一天。
等他出来的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八个半月了。”
*高瑜:我丈夫挨整七、八年,受排挤。我被调到北京市文化局,先生转业*
主持人:“他当时那个《语录》,有什么关系吗?”
高瑜:“啊,当时……你看我给讲岔了。当时给他一本《林彪语录》,你就知道当时那种政治环境,连马上要变成整人的那拨人,也不知道林彪的问题。
后来就开始陆陆续续传达了,说‘林彪折戟沉沙’、什么‘在温都尔汗给炸死了’等等,‘(林彪)叛逃’、‘要暗杀毛主席’这些罪名。
完后,空军一下就来了个‘大翻个儿’。
原来在‘干校’的……上‘干校’的那些……不是‘历史有点问题’啊,或者‘生活作风有问题’……那拨人又都回来了。
他们在部队就是这样嘛。
后来 (对) 我丈夫结束审查之后,当然要受排挤了,立刻要从空军政治部调到陕西一个机场,让他去。这时候已经挨整七、八年了。我就说’那干脆就转业吧,不在部队待了’。转业也不容易啊。正好我当时在北京市……我从外地已经调回来了。因为我弟弟在空军提干了,在广东兴宁。作为政策,我母亲就可以调回一名子女,这样我就调回来了。调回来后,我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正好我的顶头上司就是空军政委的太太,我就找她,要求我爱人转业。我说’我们不去 (陕西) 武功了’这样他 1978 年就离开部队了。”
*高瑜:我儿子小学的老师说“赵萌的妈妈真好,不跟他爸爸离婚”*
高瑜:“我儿子当时刚上小学一年级,他们的老师都特有意思,你说当年‘文革’那个影响,‘红领章、红帽徽’,突然就摘了。那会儿人没有便服啊,中国人都……他就那么那还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我儿子小学的老师说‘赵萌的妈妈真好,不跟他爸爸离婚’。
(笑)一般当时……‘文革’以后,在‘文革’当中一些婚姻很脆弱的,离婚现象比较多嘛。很多……好比女的家庭条件比较好,当年打成‘黑帮’了,下农村了,找了一个工农的,完了以后就离婚;有的女的考上大学了,男的没有,‘知青’也有这么离婚的,很普遍……
当时一看我家庭,就是那个样子吧。
后来我先生就在社会……这样我们从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我们家里边这种风波……
比较平稳呢,就是 1980 年代。反正他已经离开部队了,在建筑科学院上班,离我家也比较近。这样就一直到‘六四’,又是发生在我身上了。
所以这个‘政治运动’……我对‘政治运动’痛恨极了。”
*高瑜:我为什么没有申请入党?*
高瑜:“我为什么没有申请入党?按说我弟弟什么的都是党员,我先生也是。
我先生遇到的问题……在空军整他整到什么样子?他是很早入的党,就是 1969 年、70 年入的党吧,结果等林彪问题出来以后,(到)1977 年、1978 年,他们这派就一直挨整。”
主持人:“林彪的事情是 1971 年……”
高瑜:“1971 年哪,他们整了很多年嘛,(‘学习班’)出来以后,到 1974 年、1975 年就一直整他们。整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当时批准你入党的那个空军党委是坏党委,是错误的,所以你这个入党不算数’。
我当时受刺激这个大!我说‘你问他我们交的党费算怎么说着?你就是给我关学习班那一年,我也没少交党费呀!这个不提’。整人就整成这样。
我丈夫的档案袋还特别有意思,里边‘入党申请书’还有,批准的什么公章都有,但是同时也有一个‘撤销党员’……原因不是说他自己的问题,当然他那档案里都写‘(第)十次路线(斗争)犯错误’,写着还有说‘因为批准你入党的党委是坏党委,所以你这个入党批准的不算数’。
你说中国简直这整人……这种发明也是……一般的我看还没有过。”
主持人:“所以您一直没有提出过入党……”
高瑜:“我非常痛恨这种政治运动。”
主持人:“从来没申请过?”
高瑜:“我在文化局的时候,我那个环境特别有意思,全是人民大学的老师、人大‘支左’的解放军,而且还都是一派观点,都是‘三红’观点。
当时就是重点‘发展’我。在会上还说‘小高虽然没有写入党申请书,看来也是有这种意愿的’……就是动员我赶快写。我就因为我先生这个问题,我跟他们明确讲了,我说‘就这样的整人,你们看这种手段有多么恶劣!为这个事我也不入党,我也省得受……’
所以呢,我工作这么多年,而且在新闻界,我也没有这种枷锁。
很多人……你说在中新社,(被)整了二十年的一个老‘燕京(大学)’毕业生,因为历史问题(被)整了二十年的‘反革命’,到东北放猪还是怎么的,挨整,回了北京,慢慢稳定了以后,中新社一恢复……我就是中新社恢复时调进去的,他们这些老的……就是因为各种‘政治错误’被调出中新社的,又回来了。像这些人 1980 年代还都争取入党了。
我坚决不入。”
以上是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 2006 年来美国领奖时,接受我采访的长篇访谈录:高瑜自述人生经历,首播详细版的第四部分,在以后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请继续收听。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高瑜专辑:口述历史】系列文章
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之一)
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之二)
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之三)
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之五)
2024 年 12 月 2 日上传
本文转载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