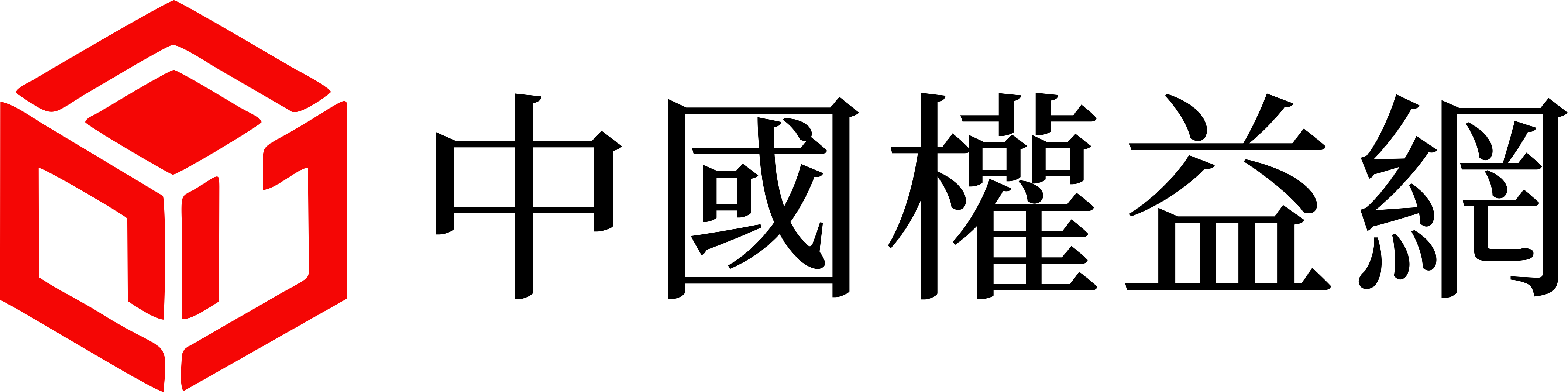2025年1月16日,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派出所向一名普通女性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理由是她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前“扰乱单位秩序”。这名女性叫尹登珍,52岁,湖北十堰人,是一位典型的“申诉访民”。在这一封公文背后,藏着一个国家如何以“维稳”为名制造冤狱、如何动用行政、公安、医疗、司法等系统联手打击公民维权的深层现实。这个案例,不是孤例,而是体制性暴力的具象演练——在中国,一位身患重病的女性公民,仅仅因为坚持表达不满,便能被暴力拘捕、黑帮式绑架、秘密关押,最终落入以“法律”包装的惩罚系统。

图为:癌症维权人士尹登珍
那一天,最高人民法院成立惩戒委员会,国家司法自诩进入“制度问责”新时代。而几公里外,一场赤裸裸的酷刑与刑讯正悄然发生。尹登珍被副所长颜廷斌反铐在椅子上,遭连续多次殴打、辱骂,并被逼迫“承认违法”,以换取保外治疗的虚假承诺。在没有任何医疗评估的前提下,警方联合医院人员篡改其确诊的淋巴癌病史,将她强行送进朝阳拘留所。尹登珍当场大小便失禁,整整七日无医无药,独自忍受身体衰竭与精神折磨。整个过程中,公安系统以“维稳”之名动用酷刑,医院配合制造“健康证明”,使一切暴力具有合法外观。这是典型的国家暴力的系统化运作:由公安主导,医疗配合,以文书合法掩盖肉体侮辱。
尹登珍遭政府绑架现场视频
尹登珍被释放那天,一场预谋中的“黑帮式绑架”正在门口上演:两辆无牌面包车、十几名黑衣人守候在朝阳拘留所门口,其中不少人戴帽蒙面。她刚一走出大门,便被人强行拖拽进黑色车辆,若非其丈夫肖书君与友人紧急营救,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场面不是偶然。三天后,北京市大兴区,清晨7点07分,尹登珍的家被六名黑衣人非法闯入。五男一女,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未穿制服,直接将她从卧室中拖拽至百米外的黑色车辆中,并掠走她的手机与随身物品。她的女儿夏贝贝报警,北京110接警单位——小红门派出所回应称:“这是地方公安带人走,不属于绑架,我们不处理。”
一句“不是绑架”,道出中国维稳模式的真正残酷之处:当地方公安可以跨省、不穿警服、无法律文书、破门而入抓人时,这已不是“执法”,而是“国家黑帮化”的典型形态。黑车、便衣、突袭、抢劫、失联,这些维稳动作与任何黑社会犯罪团伙无本质差异。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们背后是国家机器的保护伞。
1月27日,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分局通过电话告知尹登珍女儿夏贝贝,称其母亲于前一日晚间21时被正式刑拘,涉嫌“寻衅滋事”。但事实是,尹登珍在26日清晨7点就已被绑架,从北京大兴自家住宅中被黑衣人强行带走,整整十四小时后才出现法律文书。这是典型的“程序补签”式构陷:先将人控制,后补手续;先实施非法拘禁,再以“合法形式”包装暴力行为。

图为:尹登珍拘留通知书
问题在于,十堰公安的每一步操作都存在严重法律瑕疵乃至犯罪嫌疑。尹登珍在北京被抓,理论上应由北京警方发函交接、依法异地执行。但实际操作中,十堰警方既未通知北京警方,也未出具任何拘留手续、搜查证、传唤证,直接动用无牌车辆、非制服人员强制带走一名公民。此类行为,若不是警察身份,法律将其定性为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但因绑架者是公安系统人员,反而获得合法豁免。如此逻辑,直接瓦解法治最基本的形式正义。
更令人愤怒的是,面对尹登珍淋巴癌恶化的病情,十堰看守所与医院一面拒绝治疗,一面否认其病历存在。2月5日,夏贝贝携带北京301医院、武警总医院、空军总院等三家三甲医院的完整病历与影像资料前往会见,却遭告知“身体健康,适宜羁押”。狱医拒绝查看既往诊断,称“我们这里检查过了,没有癌症”。如此“医疗否认主义”,本质是国家权力对生命权的剥夺:通过否定病情,以“符合法定羁押条件”为由,拒绝保外、延长关押周期、封闭信息。
2月7日,尹登珍病情急剧恶化,被送往十堰市人民医院急诊室,却未进入普通病房,而是被秘密押往医院地下室,由十五六名狱警值守、无窗、无信号、无家属知情权、无律师会见权。这种场所已不具医疗机构特征,而是事实意义上的“黑牢”。不受司法监管、不受舆论监督,关押于此的,不只是尹登珍的身体,更是中国法律最后的尊严。

更进一步,律师提交的保外就医申请与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也均被驳回。郧阳区检察院称尹登珍“有绝食倾向、社会危险性”,认为“目前无不适合羁押的情形”,拒绝更改强制措施。这种判定逻辑极为危险——在一名被酷刑、疾病缠身、生活无法自理的病人身上,国家机关竟以“她会绝食”为理由延长羁押。这不只是官僚漠视,而是有预谋的折磨。
与此同时,尹登珍多次表示:有人威胁她必须认罪服法,否则将一并追究其女儿夏贝贝的“共犯责任”。她甚至明确指出:“他们想让我承认扰乱国家机关秩序、妨害公务、寻衅滋事三项罪名,然后判六年。我不认,就说要抓我女儿。”这已经构成变相株连,是“反右”式迫害逻辑的再现。

图为:尹登珍女儿夏贝贝 日本街头为母抗争
在尹登珍失联、病危、被刑事构陷的同时,一场真正的抵抗也在悄然进行。她的女儿夏贝贝,一位年仅二十几岁的普通女性,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也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却在短短几周内,完成了从亲属到人权抗争者的转变。她是整个事件中罕见的“明面角色”,是那个站在体制暴力与真相之间,用肉身扛起公义的人。
从1月27日尹登珍被刑拘开始,夏贝贝就启动了一系列自发的法律求助行动。她带着母亲的诊断报告和病例复印件,数次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红星派出所、小红门派出所递交报案材料,要求以“非法入侵住宅、绑架和抢劫罪”立案调查。但所到之处均遭推诿:“涉案人员中有湖北警察,不归我们处理”“我们无法确认他们是不是警察,因为没有穿制服”“你去找刑侦大队”。在中国,一个普通人若不幸成为“政治维稳对象”的亲属,便注定与所有办案机关形成一种结构性对立——你提供证据,他们否认身份;你提供视频,他们说“不清楚”;你递材料,他们说“请回去等通知”。
然而夏贝贝没有退缩。她复印了多份监控录像截图,将视频资料邮寄给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大队,并不断拨打北京110报警电话。她曾在红星派出所门口流泪恳求警员:“我妈妈是被黑社会从家里抓走的,我是她的女儿,难道你们不管?”办案警察却淡淡回了句:“那你去找湖北检察院。”
她走访检察机关、邮寄律师函、联系媒体、发出公开信,并试图通过社交网络发声,但平台迅速删除、封号、限制传播。“我发的任何一张图都立刻被清空。”她在私下对友人说。这个国家不仅要关押她的母亲,还要剥夺她讲述的权利。在她手中握着完整视频、医学报告和行政回执的情况下,竟然无法在任何一家机关得到立案的回应。这是对所谓“依法治国”的最大讽刺:一个持证公民举报绑架案,却因对方是“公安系统”而无法受理。

更为讽刺的是,湖北十堰检察院在2月25日给出的书面答复中,明确承认案发地在北京,应由北京警方处理;同时又称因未能确认抓人者身份,无法认定是否属地公安行为,建议“等北京调查后再定”。而此前,北京公安却以涉案人为“湖北警察”为由拒绝调查。两地互相推诿,案情在“管辖权逻辑循环”中被系统性埋葬。夏贝贝成为这个权力漩涡中的唯一“活人”,四处奔走,面对的却是一道道冷漠的机关门、消失的视频证据、毫无回应的报警电话。
这一切,本不应由她来承担。她只是一个想救母亲的女儿,一个普通公民,在宪法赋予的框架下寻求帮助,却被视为“扰乱秩序”的风险对象。在一个正常国家,她的行为应被鼓励、保护、支持;但在“维稳中国”,她的行动被监控、边缘化、排斥。有人私下提醒她:“你再闹,你也会进去。”律师会见尹登珍时,尹登珍亲口说:“他们说我再不认罪,就把我女儿也关进来。”
这是典型的“株连机制”——以刑法手段制约亲属,制造心理恐惧,从而击溃整个家庭的抵抗能力。尹登珍被禁锢在地下室,女儿被围困在举报死角。这不是一个案件的孤立悲剧,而是整个中国维稳体制下“家庭式报复链”的现实展演。
在最无助的时候,夏贝贝仍在坚持。她整理出自己的母亲从拘留、绑架、失联到构陷的全套时间线、证据链、医院报告,附以报警记录、官方回复函,形成一份完整的“民间调查档案”,试图突破封锁向国际媒体、人权机构投送。她说:“我不怕他们把我也抓进去,我只怕她活着被他们打死。”
她的话,是这个国家万千访民子女共同的回声。
尹登珍案之所以令人震撼,不仅在于酷刑、绑架、秘密羁押等赤裸的暴力行为,更在于它所展现出的那种“合法外观、非法本质”的国家暴力协作机制——公安、医院、检察、法院四大系统环环相扣,完成一场“从拘留到判刑”的整套构陷流程。这不是某个警察的滥用职权,也不是哪家医院的疏忽作假,而是一种高度协调、具备政治目标导向的执法黑箱。
在这个机制中,公安系统是主导者。北京小红门派出所以“扰乱秩序”为名拘留尹登珍,是整场迫害的发端;副所长颜廷斌实施酷刑,实为“审讯剧本”的标准环节。而真正决定命运走向的,是与地方政权利益更深捆绑的湖北公安系统。郧阳公安分局先是安排黑车非法绑架,再补发拘留文书,又隐瞒身份制造“无法确证”,令北京警方无法立案。这一切,若无湖北上层公安领导的直接授意,绝无可能操作得如此顺畅。
其次是医疗系统的堕落。尹登珍在301医院、307医院、武警总医院均被确诊为淋巴癌,具备严重慢性病史,按照中国《刑诉法》第75条与《羁押规定》应当予以保外治疗。但在朝阳拘留所、十堰看守所与人民医院内部,却集体否认其病情——不接收既往病历、不承认三甲诊断、不允许家属送药。这不是医疗行为,这是“维稳医疗配合”——医疗数据成为政治维稳的工具,医生不再服务生命,而是服务秩序稳定。
检察机关则承担着“程序正义外衣”的包装任务。从拒绝排除非法证据,到延长羁押时间,再到出具“社会危险性”评估,郧阳区人民检察院的每一项动作看似符合法律程序,实则是对公安酷刑、非法抓捕、秘密羁押的掩盖与背书。他们明知尹登珍被非法绑架,却不追问其“案发过程”;明知拘押程序存在严重瑕疵,却不予立案监督;明知病情危重,却拒绝变更强制措施。这是典型的“选择性司法监督”,本质上是站在国家暴力一边,与民为敌。
法院作为“最后一公里”的定罪机构,在这个系统中承担着“结果合法化”的关键作用。郧阳法院庭前会议中,律师提交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病情证明材料、提审笔录诱供证据、管辖异议全数被驳回。审判人员未作实质性审查,也未开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而是以形式主义加速庭审进度,仿佛一切已被预设。这不是真正的司法审查,而是一次由公检法主导的“审判演出”。案件未判,结局已定。
此外,司法行政系统也未缺席。三月下旬,湖北省司法局局长率队前往北京西城区司法局,要求对代理律师进行纪律追责,理由是“代理手段激烈”“散布案件信息”“干扰案件秩序”。这类行为本质上是对律师独立代理权的公然干预,意图通过跨省行政手段压制律师舆论,切断尹登珍最后的法律支援。
从行政拘留到秘密绑架,从医疗作假到检察封口,从法院驳回到司法施压,这一整套链条,不是偶然聚合,而是高度协同的维稳执行机制。它以“法治”的名义掩盖暴力,以“程序”的面具合法化刑讯,以“健康证明”制造羁押理由。其本质,是一种被国家权力整体背书的有组织系统性压迫。
尹登珍案,是当代中国“维稳国家”结构性失控的缩影:执法机关可以不穿制服、不出示证件强行闯入公民住宅;医院可以无视既往诊断报告,配合警方否认病史;检察机关可以在全案非法链条清晰的情况下继续批捕、起诉;法院可以排除一切不利于定罪的辩护与证据;而所有权力系统共同构筑的不是“司法体系”,而是一堵以“稳定”为名筑起的黑墙。
尹登珍案不是孤例。过去十余年间,中国的“维稳国家”构建出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压迫生态,其本质是对一切非体制声音的强制驯服。无论是通过行政压制、刑事构陷、精神摧残还是家属株连,这种机制都已形成高效的国家暴力系统。与尹登珍命运相似的,有2014年病亡于软禁期间的曹顺利、有因新冠报道而被捕的张展、有在“709大抓捕”中被剥夺自由的李和平——他们的共通点,是敢于发声、拒绝沉默,而国家机器的回应,是系统性地剥夺他们最基本的权利。
曹顺利当年因赴联合国培训计划前夕被失踪,之后长期羁押、延误治疗,最终病死狱中,联合国特派报告员曾就此正式致函中国政府,指出其“违反国际人权义务中的生命权与健康权”。张展则因传播疫情信息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期间绝食抗议、身体衰竭。尹登珍所遭受的身体折磨与程序构陷,与上述案例高度重合,甚至在绑架方式、就医剥夺、程序欺诈等方面更为严重。
在国际法框架下,尹登珍案已符合《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中对于“酷刑”“强迫失踪”“医疗剥夺”与“任意拘禁”的多个构成要素。酷刑不仅包括对身体的肉体伤害,也包括在押期间对必要治疗的恶意拒绝、对病史的强行否定以及借健康为名延长关押时间。这种基于健康状况操作司法流程的方式,在中国访民、异见群体、维权律师中屡见不鲜。国际社会对此类操作已有明确定性:中国正在系统性使用“准酷刑”手段对待非暴力政治异议者。
更进一步,尹登珍案还体现出“国家有组织暴力”的核心特征。第一,其过程涉及多个机关协同:公安绑架、医院作假、检察背书、法院盖章,形成了完整的压制闭环;第二,行径本身具备明显的黑帮行为特征,如无牌车辆、未着制服人员、清晨强闯民宅、掠走通讯设备等;第三,权力不受约束、责任无人承担,所有部门相互推诿、信息封锁,形成事实上的责任真空。
这一套操作逻辑,本质上已远超“执法过当”或“地方腐败”的范畴,而是一种制度内部的权力常规化暴力。它不依赖具体政策指令,而依赖体制内的默契和操作惯性。只要一个人被标记为“不稳定因素”,整个系统就能自发启动打压程序,毫无误差地完成从捕人、监禁、构陷到最终审判的全过程——且每一步都挂着“依法”的名义。
在这个体系中,个体如蝼蚁,维权者如囚徒。真正被破坏的,不仅是尹登珍的身体和尊严,而是这个国家公民社会的最低底线,是普通人与公权力之间那条本该受法律约束的边界。我们不应将其视为“特例”或“个案”,而应清醒地认识到,它是中国庞大“维稳机器”的日常输出,是一种常态化运行中的暴力逻辑。
在未来数日,尹登珍将被以“寻衅滋事罪”开庭审判。判决结果或许早已内定,但我们必须将这起案件留在舆论记忆中,将这套维稳运作流程刻印于人权档案中。我们不能让她像曹顺利那样,在沉默中死去;也不能让夏贝贝那样的人,在奔走呼号中彻底绝望。
这是我们必须铭记的案例。这是一个国家如何用法律的名义毁灭公民的样本。这是中国式维稳暴力的镜子,也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直视的真相。
编辑:孙灿星
编辑: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