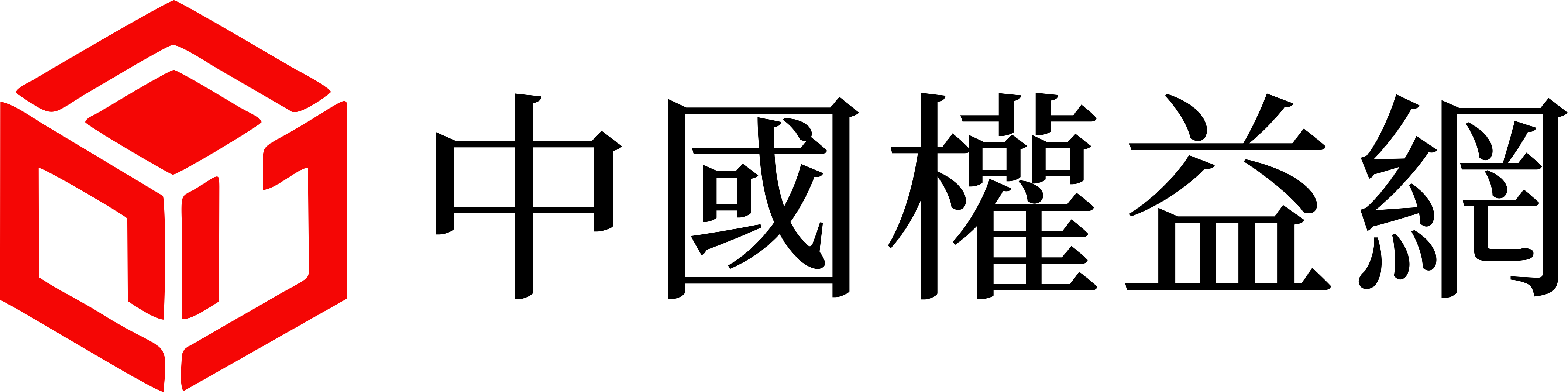王炳章:Sandel公共利益优先论批判(连载五)
第七章:“公共利益优先论”造成的另一种人间悲剧
不过,合法性的“谋私”,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即,有益于公共利益。以提倡公共利益为名,剥夺合法性谋私的权别,以“破私立公”(限除‘谋私’增进‘公共利益)为目标,并用政府公权力强制性地管控公民去实现上述“大善”,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斯大林以行“大善”、以增进“公共利益”,以把公民打造成“一心为公共利益”的、有集体主义先进思想和美德的模范良民为目标,强制性实施“集体农村”制。因为“小农经济是培养‘谋私’的落后小农思想的温床”。结果,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正如前苏共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集体农庄下,农民成了新农奴”。因为,农民在没有签订任何契约的情况下,被斯大林赶进集体农庄,农民们不进入”集体农村”不行,退出”集体农庄”, 也不行”。实践证明,如若你的“公共善(public good)”,强调的是劳动总成果的“结果分配平均主义”,那么,你的“公共善”,盖起来的,可能是座人间地狱。强调“果实分配均等”的集体农庄,导致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最后,都不出力,粮食欠收……。
我想到那个时代的两位世界级知名作家。一名是法国的罗曼·罗兰 (Romain Ralland),另一名名是爱尔兰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两位受到斯大林虚假宣传的影响,响往斯大林主义,前去朝拜。他们看到的,是被斯大林精心化妆、立为样板的“集体农庄”。被忽悠的这两位“聪明人”,回到欧洲,为斯大林歌功颂德。他们这么干,给自己的生涯留下了一个助纣为虐的污点。我之所以说一下这两位名人,乃想告诫某些人,别再重复这两位的错误,被某些大恶掌权人“乔装打扮”的供人“参拜”的样板所迷惑。
(二)上世纪1975年后的一段时间,[1]柬埔寨由波尔布特政权统治。波尔布特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听起来这具有非常的“公共善”。“公共善(public good)”不就是追求“公民人人平等”吗?波尔布特集团实施非常极端的“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用公权力实现“三无社会”:(一)无货币(因为“钱是万恶之源”);(二)把城市大批人赶到农村而形成无城乡差别(因城市是资本家的大本营);(三)无“知识份子——工人——农民”收入上的差别:一律实行配给制(因为差别收入就是不平等)……。(当然,后来,波尔布特也不得不印钞票[货币],因为,无货币,社会运转不了……。但在当初,他的确想永远消灭货币)。尔布特等,想一步迈入“共产主义的天堂”……。“共产主义”,其实今日世界上有一个挺好、值得大家去看看的“共产主义社会”——以色列内的“基布兹”(又称为共产主义实验区)。它欢迎世界各地人自由参与,自由出入。以前曾是“无货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样的学校……”。近年,实行了改革:实施“土地包产到人,个人收入与工作情况挂钩……等”。它之所以能改革,因(一)改革是社区全体公民投票决定的;(二)社区每个公民一票,机会与权利均等地立法,竞选;(三)它自由进出,依契约而行……。我要表达的是,人类不怕试验,不怕犯错,怕的是没有契约自由;要的,是平等的机会,权利被当政者用权力剥夺……。一步迈进“共产主义”,怎么行得通呢?反对声起。“反对?那不是反对人人平等吗”?不是“邪恶”吗?此恶,怎能存在?应清除之。——于是,开始杀人。不久大规模集体屠杀开始了……。恐怖之极。
20多年前,我去柬埔寨考察,亲眼去看过离金边不远的一个“万人坑”。那里,已修围墙,有几个大坑,坑边盖了一座透明的亭楼,
里面堆满了白骨:有儿童的、有妇女的……。令人毛骨耸然。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他们在全柬埔寨170个县中的80个县进行了勘察,挖掘了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具骷髅。法国学者吉恩.拉古特发明了”自族屠杀”。像这样的“万人坑”,可能还有一些未被发现的。就是说,至少有150万多无辜,残遭杀害。其中,华侨被杀者人数,以人口比例而计,在柬埔寨所有民族之中,是最高的。因为,华侨重视教育,勤劳致富者很多。而知识份子是波尔布特改造的对象,富人是他要消灭的对象。我在美国,见到过当年从柬埔寨逃难出来的一些华侨。说到那段恐怖的经历,有的不停地流泪,有的泣不成声。因为,他们不少亲友惨死在波尔布特党徒的枪下。他们对当年支持柬国执政的外国政府2及政要也大加鞭笞。有人说,遭屠杀的柬埔寨国民,占当时总人口的1/5左右.
(三)1984年,埃塞俄比亚掌权者强力推行类似前苏联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制度,数百万人饥饿而亡,国家陷于内战。推行此制度的原由也是为了实现“公共的善”这一类的美好目标。……
说明一,上面,我仅举了三例。现实是,类似的例子有不少。我想,这三例已足以说明问题了。
说明二,Sandel,教授,我似乎从来没听你说过你主张“个人善和个人利益”(individual good——individual interest [benefit]),而你四处宣传的是“公共善——即公共利益”(public good [benefit])。[2][3]
public good, social good,这三个词儿,其实质,是一码事。实际上,你说来说去,上面三者,都可涵盖在“社群整体善”或“社群整体利益”(Social collective good [benefit])这一词儿之下。
我记得,我在听某些英文课时,公共利益,通常用“public good”表达。象处理垃圾问题,就是一个 public good(公共利益)问题。
又如;cuts have been made for the good of the company(裁减的实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等。因此,good可当利益用;虽然,good的涵义比Benefit要广些。
我想先清晰概念(或者说,是表达方式):
一是“good”的表达方式(概念)。不论依英文解说,还是依中文解说,“公共善(public good)”是抽象表达;而有“公共利益(public benefit [interest])”是具象(具体)表达。用具象(具体)表达,更大众化,更好懂。的确,不给广大公民带来具体利益、具体实惠的“善”,老百姓不欢迎。象你Sandel教授这样的“大学者”喜欢用抽象的学术化的大词儿,如“good”。这样作,显得“你有学问”和与众不同。我不,我喜欢用接地气而老百姓都懂的小词儿,如,interest(benefit)。good,俗称,就是好,好处。
二是“public”的表达方式(概念)。 public的意义,主要讲“是大众的,群体的”。但是,“public school”在英国(尤其在England),指的是“private”学校——专供13~18岁学生寄宿而自费的学校。因此说,“public”这个表达方式(或日public这个概念),在个别情况下,也会引起误解。因此,中国在翻译这。种学校时,使用了“公学”这个词儿,而不好用“公立学校”这个词儿。
<span;>或问:你这个人对概念这么“叫真儿”干么呢?我的回答是,讨论哲学问题厘清概态,是个大事儿。你看, Sandel教授为了表达清楚“public”这一概念,用了“social(社会的)”、“common(公众的)”、“社会整体的(social collective)等许多近义词儿。因为,他怕用一个词儿说不清楚。
<span;>这说明什么呢?我不客气地说,这说明,Sandel教授的哲学功底(或日哲学表达功底)不深。甚至可以说,他自己没弄懂“哲学”这门科学为何物。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用准确清晰而又高度抽象的概念来阐述表达事物的普通(或日“一般”)特性及规律。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Sandel教授反复用了很多近义词儿来表述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怕厘不清晰他要表达的“public”这个概念而误解他。其实呢,想要表达清晰一个概念而不致混淆,最简直的表达方法,是:把这个概念相对(或曰相反)的概念讲出来就行了。——这比你用相近的多个概念来定义它,既省事又明白。如,你说“public good(公共善)”,你指出,“这里的“public”,是针对“individual(个人)”而言的。一下子,大家就明白了。这是我为什么在前面说,我没听你说过’你主张个人善和个人利益’的原因之一。我要在此讲的是一个“很大的哲学问题”:当你想清晰而简洁、不让别人误解你讲的一个概念时,你特别强调一下(或同时指出并说明)这个概念的相对(或日相反)概念就行了。
<span;>比如,你对刚懂事儿的小孩儿说“你是女的(或男的)”,你说十遍,她(他)也不见得明白。但是,你跟她(他)说:“你妈妈是女的,你爸爸是男的。你和妈妈(或爸爸)一样,是女的(或男的)”——她(他)一下就记住了,明白自己的性别了(当然,男、女定义的细节和生理学区别,等孩子的认识能力提高到相应程度时,再讲。此乃常识)。又如,你讲“黑”的概念及黑色的物理学特点时,与“白”的概念及白色的物理学特点来对照讲,学生就会很清楚而且记得牢。
<span;>针对 Sandel教授,表达概念的“反复性、用了很多近义词儿”的情况,我可以判断, Sandel教授在认知上,在表达上,存在着很大盲区(任何人都有认识盲区,我也不例外),他甚至不知道“用对照性概念。
<span;>《圣经》中“挪亚方舟”的故事,非常有名。不仅西方知道,一般东方人也知道。但是,挪亚为何先放乌雅(鸦),后放鸽子?——此问题,在我之前,无一人能给出合理解答,包括西方所有的《圣经》学者。
<span;>我的的物理学,生物学,不错;也懂“哲学上概念的对照性表达之理。我看了数遍“挪亚方舟及放鸟鸦、鸽子”的故事后,我很快悟出了,鸟鸦是黑色、而黑色是全光色吸收者;而鸽子(信鸽)是白色、是全光色的反射者”——先祖用乌鸦的道理之一,是“指”,法律的建构要顾及(考虑到)所有宪政角色(颜色是表达角色的最佳方式之一)的职责;而法律的使用要顾及(考虑到)所有宪政角色职责的发挥——这是用鸽子的道理之一。当然,这只是认知的浅层,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详见我别的著作。《汉穆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石上,——这是有讲究的。其理,应说清楚,详见我另外的著作。
<span;>讲清楚哲学概念的道理。除了“public”乃针对“individual”而言外,Sandel也不知道,你要说清“善”,必须也要说清“恶”这个“对照性阐述”的道理(详后)。
<span;>善用或曰“必用”“对照性概念”来使对方明白你说的概念本义,不但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在日常交流中,也很有用。举例。我到西方后,对西方人讲“我们在中国时,在教育上,强调“集体主义,集体利益”。有人向:什么叫“集体主义和集体利益的‘集体’”?你们怎么定义“集体”?我说,我们讲的集体: (collective)就是针对个体(individual)而言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就是说,由于表达习惯等问题,我们在中国讲的“集体善(或曰集体利益—— collective [ group] benefit [interest])”,与 Sandel教授说的“public good(公共善)”“公共利益”,其实是一码子事。我们以前在中国(还有其它一些国家),不常用“公共利益”这个词儿;除了常用“集体利益”外,有时也用“国家利益”这个词儿——国家是个集体。国家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另外一种近义性表达。
<span;>但是,我说“Sandel教授在概念的阐述上,在表达上有盲区” ——并非我想批评一下 Sandel教授的重点,这只能算一个“小批”。我对Sandel教授的“大批”是什么呢?有人听了可能感到有点奇怪与不解:我对Sandel的“大批”是“大批”他对“公共善(或曰公共利益)的“情有独钟”,是Sandel有意地忽略与抵制“个体利益”而主张“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我为什么要“大批”他这个“情有独钟”呢?请听我的分析。
<span;>[1]波尔布特集团即红色高棉于1975-1979年初掌权。
<span;>[2]Sandel教授你用的共同善、公共善、社会善—— common good,
<span;>[3]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但我喜欢研究英语。
<span;>第八章:Sandel教授与希特勒都是“公共利益”的宣传者
<span;>近代史上,对公共善,或曰公共利益(public benefit [interest])“情有独钟”者,有不少。
<span;>請看官们猜猜讲下面这两段话、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是谁?
<span;>1)A者说:“XX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XX主义是什么主义,见下面)。
<span;>2)B者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輕重的,个人位置的确定,只取决于民族的利益,任何骄傲自满的情绪,任何认为个人至上的想法,不仅仅是可笑的,而且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决定个人利益的范围并决定个人的义务。
<span;>你猜到了吗?答案是,
<span;>第二位(B者)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是希特勒,德国“国家国[2]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1]党魁(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
<span;>第一位(A者)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戈林(Hermann Goring)。“XX主义”,指的是“纳粹主义”。
<span;>还有,斯大林、波尔布特等人,都是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这些杀人魔王,有几个共同点他们都有几个情有独钟。(一)一是对达尔文人类进化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情有独钟;(二)二是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三)三是对“公共利益(public good)”,情有独钟。
<span;>[1]请Sandel教授注意:希特勒是信仰“社会主义”的。
<span;>[2]“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国家”,也有译成“民族”的,称“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t的缩写Nazi之音译。
<span;>[3]社会主义(Socialism),针对资本主义(Capitalism)而言。
<span;>说明:我也认为“社会主义”挺好。但是,要审视他搞的“社会主义”之实质内容。从“社会主义”一语发明至今,有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出现。社会主义,多理解为“与平等”之义相关。平等,可分为若干类,(一)如果“平等”强调的是公共自然资源与公共社会资源在起始时“公民人人分配上的平等”,如中国安徽省小岗村“依人均分配土地”(自然资源);如加拿大等“依公民人人均等的原则,分配医疗资源”(属于公共社会资源),使山沟农夫与政府高官所享受的医疗待遇,完全平等。这种“社会主义平等”,我举双手赞成。(二)强调社会(公共)成果上的分配平等。这种主张平等的“社会主义”,要高度警惕。弄不好,导致大悲剧。(三)假“社会主义”之名,掌权者大搞特权——如,斯大林时代,政府一小部分高官及其家属(占总人口不到2%),占有并享受全国公共医疗资源的80%左右。剩下的20%左右,则平均分配给近2亿公民。如此特权社会主义,应加以反对。(四)借“社会主义”之名,搞专制独裁,也应反对。
<span;>Sandel教授,你主张的社会善(Social good)的社会(Social)词儿,将之“主义化”(理论化、制度化),就是“Socialism”(社会主义)。
<span;>我知道,你Sandel教授,肯定不愿意与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这些人为伍。但是,你的“公共利益——公共善(public good——public interest [benefit])”之主张,都与上述这些魔鬼式人物相同。你们都有“公共利益为上”的情结。
<span;>Sandel教授,我还要请你注意一下我上面举出的“前苏联斯大林强力推行的集体农庄”、“前埃塞俄比亚总统拷贝集体农庄”。“前柬埔寨波尔布特强行的平等”——这三个例子。此三例都是以实现“公共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施行的。结局都是以酿成悲惨结局而收场,都造成了本国公民百万以上,甚至几百万的非自然死亡。上面我也说了,现实中的例子,决不止这些,在全球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远比这些数目为大。全球此一数字到底是多少?我处资料很有限。请 Sandel教授及朱慧玲博士与 Sandel同校的杨建利(Yang Jian Li)博士[1]联系一下,我记得他对此问题曾有过研究,并通过杨博士请教一下近代史专家辛灏年教授,他们或可给你一个答案并提供文献支持。
<span;>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上面三国及全球相关其它地区类似事件,还有1845年爱尔兰饥荒事件及类似事件……,从“善”意出发,及或以“公共善——公共利益(public good——public interest [benefit])为名所造成人类非自然死亡人数(注意,我并未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一切军事大战造成死亡的人数),比相同时间段[2]在同一地区中,由那些明火执杖的江洋大盗故意犯罪而致死的人数,多十倍而不止。
<span;>所以,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学者,对鼓吹“善”和“公共利益”,应该非常慎重。其他学者和民众,同时要对这种鼓吹“善”和“公共利益”的人(不论是学者、还是政客),要有着高度的警惕性。从 Sandel教授所写所说的来看,他似乎对此毫无认知,也缺乏对这方面资料的阅读与知识积累。
<span;>• Yang JianLi 祖籍中国山东。1991年在栢克莱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并于200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span;>• 我说的“相同时间段”与“同一时间段”,不是同一概念。以爱尔兰1845年马铃薯瘟疫事件导致立法大错为例,恶法令颁布后“半年内造成了大批公民饿死”。“半年”,这个时间段。“相同时间段”——半年,并非指此法令后的那半年,而是.指(下面只是举例)例如1840年中的“半年”(未有饥荒)这种时间段。
<span;>2024.8.30